|
張航,趙兵濤,劉旺
(上海理工大學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上海200093)
摘要:為探究藻類生物質燃燒過程中SO2與CO2的排放特性,利用管式爐對典型藻類生物質條滸苔、馬尾藻和小球藻在不同溫度及配比下燃燒時SO2與CO2排放特性進行了實時在線測量,并進行了S、C轉化機理的初步分析。結果表明,隨著溫度的升高,燃盡時間縮短,SO2與CO2實時排放量增加。隨著生物質量的增加,藻類生物質燃燒時SO2與CO2排放量增加,但排放量增加幅度不同。當生物質質量為75mg、150mg、225mg時:馬尾藻SO2排放量分別為0.18mg、0.30mg、0.31mg,CO2排放(體積分數)分別為2.47%、4.81%、6.42%;條滸苔SO2排放量分別為1.14mg、2.61mg、3.95mg,CO2排放(體積分數)分別為3.16%、5.05%、8.32%;小球藻SO2排放量分別為0.79mg、1.93mg、3.92mg,CO2排放(體積分數)分別為4.71%、6.75%、13.26%。藻類生物質混燒的結果表明,當小球藻、條滸苔以及小球藻、馬尾藻等比例混燃,在800℃時SO2排放總量均降低,混燃樣品自身含硫量以及堿金屬元素含量對SO2排放影響較大。
生物質作為一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具有可再生、儲量大、分布廣等特點[1-3]。燃燒是生物質能源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來,針對生物質燃燒過程中污染物排放特性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例如,通過林木類與農業類生物質燃燒及對比試驗揭示了生物質燃燒污染物排放特性[4-5],為生物質的合理利用提供了指導,還有對垃圾類生物質燃燒過程中煙氣污染物的控制工藝進行分析[6],此外,還包括對多種固體生物質燃料的燃燒利用以及污染物排放特性的綜合研究[7]。
但是,與常規生物質不同,水生生物質尤其是以藻類為代表的新型水生生物質,具有生長周期短、繁殖快、可模化利用等特性[8]。目前對其干態化能源利用的方式局限于熱解、燃燒性能和灰熔融特性等方面的研究[9-12],而對其燃燒過程中污染物的排放特性尤其是硫氧化物與碳氧化物的排放特性的研究較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進行了典型藻類生物質在管式爐內燃燒時SO2與CO2排放特性的試驗。著重研究了溫度、生物質量以及配比混燃對其燃燒硫氧化物與碳氧化物排放特性的影響,從而為藻類生物質干態化規模利用提供參考。
1實驗設備材料及方法
1.1實驗設備及材料
如圖1所示,燃燒裝置為管式爐反應器,反應器為外徑40mm、內徑30mm的剛玉管。實驗材料為山東省無棣縣小球藻(Ch)、浙江省寧波條滸苔(En)、海南省馬尾藻(Sa)。3個藻種平均粒徑D50分別為86.8µm(Ch)、87µm(En)、88µm(Sa)。3種藻類元素分析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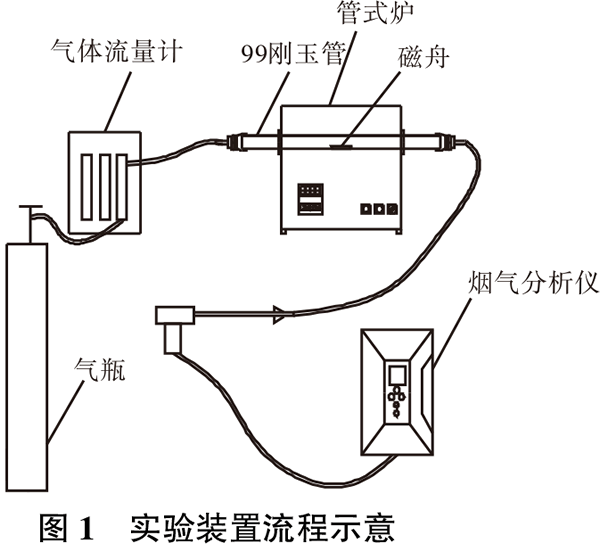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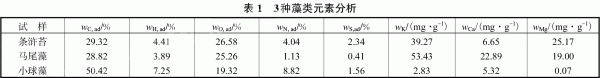
1.2試驗方法
將管式爐升溫至實驗所需溫度(600℃、700℃、800℃和900℃),通入3L/min標準空氣,待溫度和氣流量穩定后,稱取實驗樣品100mg,置于瓷舟內平鋪,然后迅速將瓷舟推送至爐管中央恒溫加熱區,快速封閉端口,燃料在爐管內恒溫燃燒。使用Testo350測定燃燒煙氣中SO2、CO2實時排放濃度,同一工況下做3組平行實驗,得出實時均值誤差曲線。
2結果與討論
2.1溫度的影響
2.1.1 SO2排放特性
如圖2所示,馬尾藻與條滸苔SO2實時排放曲線為雙峰,小球藻為單峰。3種藻類在反應進行到25s時,均達到第1個SO2排放峰。馬尾藻燃燒時SO2實時排放量最低,最大峰值為0.088mg/L,條滸苔燃燒時SO2實時排放量相對較高,最大峰值為0.81mg/L;小球藻排放最高,900℃時達到0.96mg/L。
藻類生物質燃燒過程中有機硫分解主要發生在揮發分燃燒階段,無機硫的分解發生在焦炭燃燒階段[13]。所以3種藻類達到第1個SO2排放峰所需時間大致相同。由表1可知,馬尾藻與條滸苔堿金屬元素含量較高,可以推斷兩種藻類硫的賦存形式除了有機硫和單質硫外,無機硫含量較高。500℃以上時,生物質自身賦存的部分無機硫酸鹽可發生分解,以有機硫或無機硫化物的形式吸附于焦炭結構中,在焦炭燃燒階段,自身賦存以及分解轉化的無機硫化物和附著于焦炭結構上的有機物發生氧化反應,部分以硫酸鹽的形式固存于焦炭結構中,部分以SO2形式析出[14]。而小球藻堿金屬含量較低,硫的賦存形式主要為有機硫和單質硫,焦炭燃燒階段SO2排放量較少。因此,馬尾藻與條滸苔燃燒SO2排放為雙峰分布,小球藻為單峰。揮發分燃燒階段有機硫分解排放所需溫度較低,馬尾藻S含量較低,且富含的堿金屬元素進行的固硫反應又降低了SO2的排放量,故馬尾藻SO2實時排放量較低。條滸苔與小球藻S含量較高,尤其是小球藻堿金屬含量較低,因此其SO2實時排放量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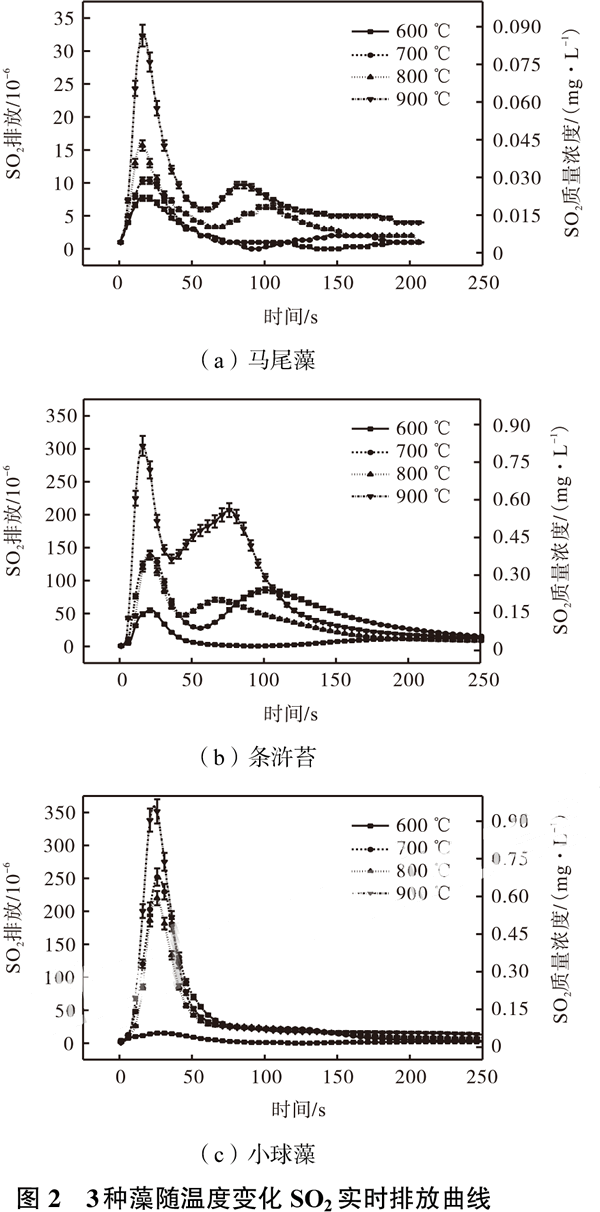
隨著溫度的升高,馬尾藻與條滸苔第2個SO2排放峰總體上提前,說明溫度越高,反應越易進行,達到峰值所需時間越短。600℃時,3種藻類SO2實時排放量都比較低,在700~800℃范圍內,隨著溫度的升高,馬尾藻與小球藻SO2實時排放量均增加,條滸苔SO2實時排放量基本不變,900℃時3種藻類SO2實時排放量都有明顯增加。這可能是由于600℃時藻類燃燒不充分,緊密結合的有機硫以及結構穩定的無機硫無法分解排放,同時部分氣相含硫化合物與生物質中的堿金屬元素結合,以硫酸鹽的形式固存在焦炭結構中[15],因而600℃時,3種藻類SO2實時排放量都較低。當溫度在700~800℃區間內增加時,由于馬尾藻SO2實時排放濃度較低,小球藻堿金屬元素含量較低,根據化學反應動力學,這兩種藻類生物質燃燒過程中固硫反應速率都比較低,對SO2排放量的影響較小,隨著溫度的增加,結構穩定的有機硫以及無機硫逐步分解、排放,導致SO2實時排放量增加。條滸苔硫元素以及堿金屬含量都比較高,SO2實時排放濃度較大,燃燒過程中二次固硫反應對SO2排放的影響較大,而且溫度越高固硫反應越易進行,因此條滸苔在700~800℃溫度范圍內燃燒時,隨著溫度增加SO2實時排放量變化不大。900℃時,自身賦存以及二次反應固存于焦炭中的硫酸鹽易與燃料中的Si、Ti結合,形成硅酸鹽和鈦酸鹽,從而導致SO2析出[16],導致SO2排放量增加明顯。
燃燒溫度在600℃、700℃、800℃、900℃時,隨溫度的提高,馬尾藻與小球藻S轉化率提高,馬尾藻轉化率分別為:6.59%、8.78%、16.34%、37.44%,小球藻轉化率為10.10%、44.46%、51.67%、60.64%。條滸苔在800℃燃燒條件下,由于固硫反應增強對SO2的減排量明顯高于溫度增加所造成的SO2排放量的增加量,導致其800℃時S轉化率降低,隨溫度的增加,條滸苔燃燒過程中S的轉化率分別為15.98%、43.76%、32.52%、70.36%。
2.1.2CO2排放特性
如圖3所示,反應進行到25s時,3種藻類均達到第1個CO2排放峰。馬尾藻燃燒時CO2實時排放量最低,CO2排放峰均小于4%,其次為條滸苔,最高CO2排放峰為4.8%,小球藻燃燒時CO2實時排放量最高,900℃時峰值達到了最大的8.3%。主要原因是在揮發分燃燒階段,碳元素隨有機物的氧化分解以CO2的形式排放所需溫度較低,因此3種藻類在各溫度下達到第1個CO2排放峰時間相同。由表1可知,wCCh>wCEn>wCSa,燃料燃燒CO2排放量與C含量相關,而且馬尾藻與條滸苔賦存的堿金屬對CO2的固存作用會降低CO2排放。
馬尾藻在600℃和900℃時燃燒,CO2排放的雙峰趨勢明顯,條滸苔隨著溫度升高雙峰趨勢增強,小球藻在600~800℃范圍內,隨著溫度升高,第2個CO2排放峰增強,900℃時減弱。燃燒過程中,生物質中的C主要以CO、CO2、CxHy的形式排放[17]。馬尾藻堿金屬元素含量較高,可以推斷其生物質自身無機物賦存量較大,600℃時,燃燒不充分,耗氧量較低,在燃燒氣氛中氧含量較高的情況下,C主要以CO2形式排放[18],因此,600℃時,在焦炭燃燒階段CO2實時排放量較大。700~800℃時,隨著溫度的升高,無機物的氧化分解會消耗部分氧氣,氣氛中氧元素的降低使CO2生成反應減弱,而且隨著溫度的升高,馬尾藻富含的Ca易與CO2結合,以碳酸鈣形式固存于焦炭結構中,因此,在700~800℃燃燒條件下,焦炭燃燒階段實時CO2排放量降低。900℃時,馬尾藻自身賦存以及二次反應固存于焦炭結構中的碳酸鹽會分解,導致CO2實時排放量增加[19],因此,在600℃以及900℃時,馬尾藻燃燒時CO2排放雙峰趨勢明顯。條滸苔K、Mg含量較高,K2CO3不分解,MgCO3在350℃即可分解,排放出CO2[20],溫度越高,焦炭燃燒階段燃燒反應越充分,CO2實時排放量越大,因此,條滸苔隨著溫度升高,雙峰趨勢增強。小球藻在600~800℃范圍內,隨著溫度升高,在焦炭燃燒階段,緊密結合的有機物逐漸分解釋放,CO2實時排放量增大;900℃時,由于小球藻堿金屬含量較低,可分解釋放的碳酸鹽較少,而且在此溫度下焦炭易將CO2還原成CO,因此,在900℃時,焦炭燃燒階段的CO2實時排放量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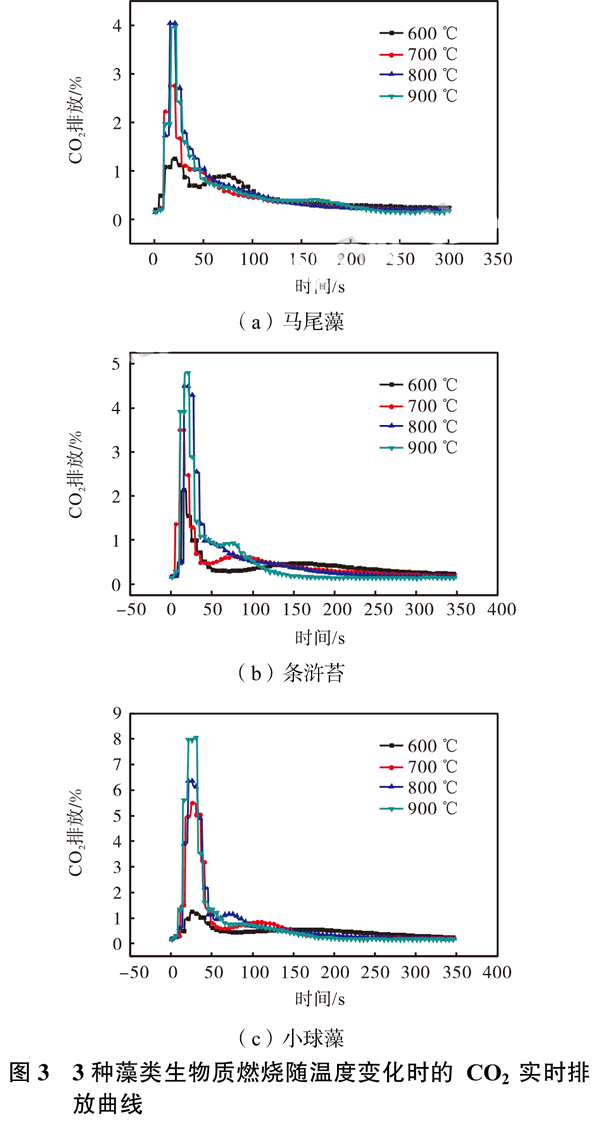
2.2生物質質量對SO2與CO2排放特性的影響
3種藻類生物質結構和成分上的不同導致其燃燒過程中各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存在很大差異。因此,本文進一步探究不同生物質的質量對藻類生物質燃燒時SO2與CO2排放特性的影響,溫度設定為800℃。
如圖4所示,隨著生物質質量的增加,馬尾藻燃燒時SO2與CO2排放量均增大,但是排放量增加幅度降低,而且在焦炭燃燒階段SO2排放量增加幅度降低更明顯。原因是馬尾藻K、Ca含量較高,隨著生物質量的增加,SO2與CO2排放增加,促進其與生物質內富含的K、Ca結合以硫酸鹽及碳酸鹽的形式固存于焦炭結構中,使燃燒過程中由于生物質量的增加所增加排放的CO2與SO2被部分抵消,而且此類硫酸鹽與碳酸鹽結構穩定,在900℃以上才會發生分解[20],因此隨著生物質量的增加,SO2與CO2排放量增加幅度均降低。焦炭燃燒階段多孔性焦炭結構增加了固硫反應面積,而揮發分的析出減少了固硫反應時間[21],導致焦炭燃燒階段SO2排放量增加幅度明顯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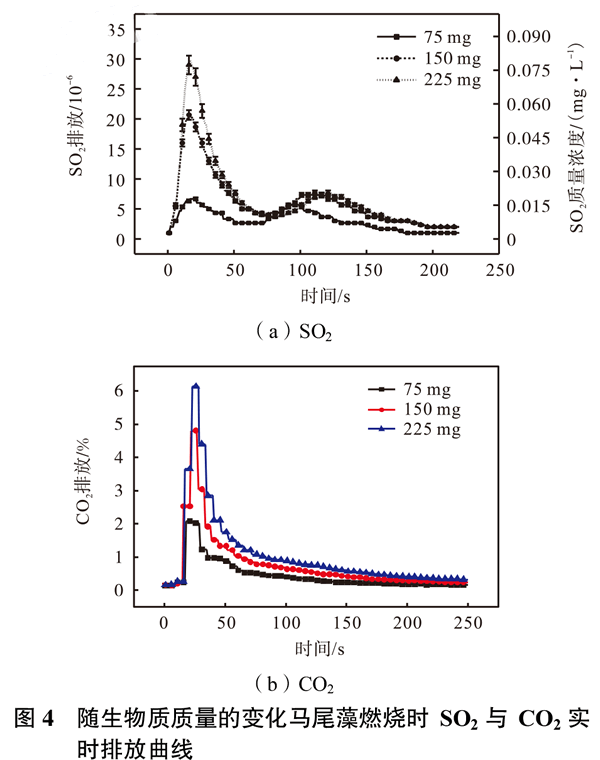
如圖5所示,隨著生物質量的增加,條滸苔燃燒時SO2與CO2排放量均增大,燃燒過程中SO2與CO2的排放量增加幅度變化不大。這是由于條滸苔內硫元素以及堿金屬元素含量都比較高,生物質燃燒污染物的排放特性受燃燒溫度、賦存形式、堿金屬元素含量以及氣固兩相反應等因素的影響[22],由于各元素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燃燒過程中各種抑制或增強反應大致抵消,導致條滸苔隨著生物質質量的增加,SO2與CO2以一定的排放率排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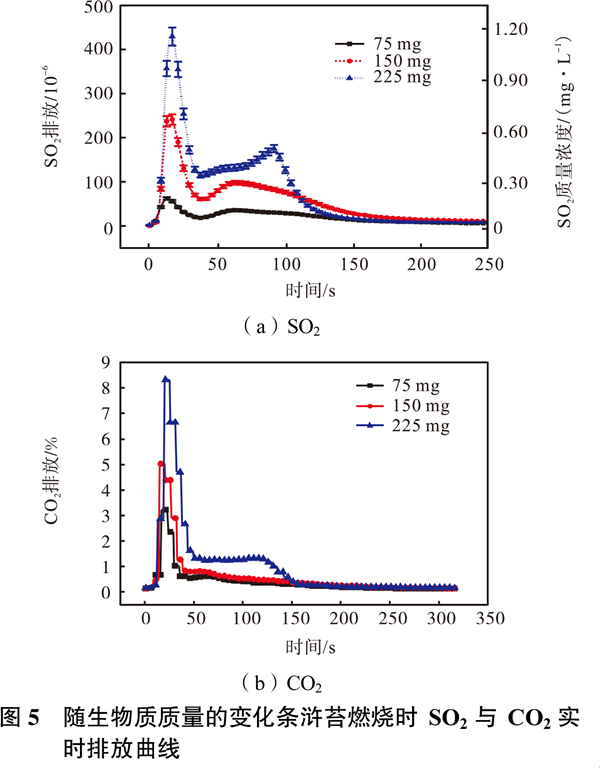
如圖6所示,隨著生物質質量的增加,小球藻燃燒時SO2與CO2排放量均增大,且燃燒過程中SO2與CO2排放量增加幅度也隨之升高。這可能是因為小球藻內堿金屬含量較低,燃燒過程中SO2實時排放濃度較高,可以推測出硫的賦存形式以有機硫所占比重較大。在800℃燃燒條件下,有機硫能夠迅速分解排放,隨著生物質量的增加,劇烈的燃燒及排放導致氣氛中生成的SO2與CO2不易擴散至焦炭表面與焦炭結構內的Ca結合轉化成結構穩定的硫酸鹽及碳酸鹽,使C與S固存率降低,從而導致小球藻隨著生物質量的增加,燃燒過程中SO2與CO2排放量增加幅度均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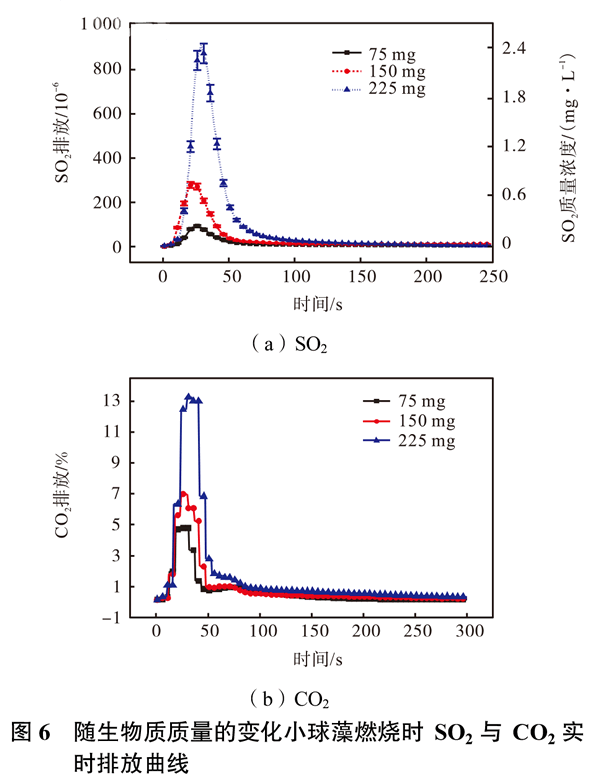
2.3混燒排放性能
如圖7(a)所示,小球藻與馬尾藻等比例混燃樣品在800℃條件下燃燒時SO2排放總量降低。原因是小球藻燃燒時SO2實時排放體積分數較高,馬尾藻堿金屬元素含量較高,兩種藻類生物質等比例混燃時,燃燒氣氛中高體積分數的SO2以及焦炭結構中含量較高的堿金屬元素促進了固硫反應的進行,溫度越高反應越易進行,而且SO2與馬尾藻富含的K、Ca結合所形成的K2SO4及CaSO4在800℃時能夠穩定存在[23],因此,混燃樣品在800℃燃燒時SO2排放總量降低。同一溫度下,隨著小球藻配比的增加,SO2排放總量增大。說明了藻類生物質燃燒時SO2排放總量與硫含量相關,堿金屬元素含量也有一定影響。

如圖7(b)所示,小球藻與條滸苔等比例混燃樣品以及單一條滸苔在800℃條件下燃燒時,SO2排放總量均降低,主要是因為小球藻與條滸苔S含量都比較高,而且條滸苔堿金屬含量較高,燃燒過程中生成的高體積分數SO2使固硫反應劇烈發生,導致其在800℃燃燒時SO2排放總量降低。與小球藻單獨燃燒相比,在800℃時,由于小球藻與條滸苔等比例混合樣品燃燒堿金屬元素所固存的SO2量高于其自身硫含量的增加所造成的SO2排放增加量,因此,小球藻與條滸苔等比例混燃樣品燃燒時SO2排放總量低于小球藻單獨燃燒時的SO2排放總量。
如圖7(c)所示,隨著溫度的增加,條滸苔與馬尾藻等比例混合樣品燃燒時,SO2排放總量遞增。原因可能是隨著溫度的增加,燃料燃燒充分,導致SO2排放量增加幅度高于固硫反應增強造成的SO2減排幅度。
3結論
(1)隨著溫度的增加,3種藻類生物質燃燒時SO2與CO2實時排放體積分數呈遞增趨勢,但條滸苔在800℃時SO2排放總量降低。
(2)生物質量的改變對藻類生物質燃燒過程中SO2與CO2排放特性影響與生物質硫的賦存形態以及堿金屬含量有關。當生物質質量在75mg、150mg、225mg時,馬尾藻SO2排放分別為0.18mg、0.30mg、0.31mg,CO2排放分別為2.47%、4.81%、6.42%;條滸苔SO2排放分別為1.14mg、2.61mg、3.95mg,CO2排放分別為3.16%、5.05%、8.32%;小球藻SO2排放分別為0.79mg、1.93mg、3.92mg,CO2排放分別為4.71%、6.75%、13.26%。堿金屬含量較高的馬尾藻與含量較低的小球藻呈現明顯差異。
(3)混燃時,SO2排放總量與藻類生物質特性和燃燒條件呈現相互影響的復雜關系。SO2實時排放體積分數高的藻種與堿金屬含量較高的藻種等比例混燃時,在800℃燃燒條件下,SO2排放總量降低。
(4)由于藻類燃燒過程中硫、碳等污染物排放的影響因素較多,其他因素(包括顆粒粒徑、氣氛組成等)對藻類生物質燃燒污染物排放特性的影響尚需要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馬廣鵬,張 穎.中國生物質能源發展現狀及問題討論[J].農業科技管理,2013,32(1):20-23.
[2]魏 偉,張緒坤,祝樹森,等.生物質能開發利用的概況及展望[J].農機化研究,2013(3):7-11.
[3]BP Group.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EB/OL].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2014-06-22.
[4]彭徐劍,胡海清,李敖斌,等.東北三大硬闊燃燒過程煙氣排放特征[J].森林工程,2012,28(3):6-11.
[5]Brassard Patrick,Palacios Joahnn H,Godbout Sté-phane,et al.Comparison of the gaseous and particulate matter emissions from the combus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biomasses[J].Bioresource Technology,2014,155:300-306.
[6]王文剛,付曉慧,王學珍.生活垃圾焚燒煙氣污染物控制工藝選擇[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4(3):87-91.
[7]Williams A,Jones J M,Ma L,et al.Pollutants from the combustion of solid biomass fuels[J].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2012,38:113-137.
[8]王 寧,王 爽,于立軍,等.海藻的燃燒特性分析[J].鍋爐技術,2008,39(2):75-80.
[9]劉樹煒,吳創之,趙增立.海藻熱解動力學特性研究[J].能源工程,2008(1):11-15.
[10]趙 輝,閆華曉,張萌萌,等.海洋生物質的熱解特性與動力學研究[J].生物技術通報,2010(4):135-140.
[11]王 爽,姜秀民,王 寧,等.海藻生物質灰熔融特性分析[J].中國電機工程學報,2008,28(5):96-101.
[12]王 爽,姜秀民,王 謙,等.海藻生物質顆粒流化床燃燒試驗研究[J].化工學報,2013,64(5):1592-1600.
[13]Dayton D C,Jenkins B M,Turn S Q,et al.Release of inorganic constituents from leached biomass during thermal conversion[J].Energy Fuels,1999,13(4):860-870.
[14]柏繼松.生物質燃燒過程氮和硫的遷移、轉化特性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院,2012.
[15]Knudsen J N,Jensen P A,Lin W G,et al.Secondary capture of chlorine and sulfur during thermal conversion of biomass[J].Energy and Fuels,2005,19(2):606-617.
[16]van Lith S C,Violeta Alonso-Ramírex,Peter A,et al.Release to the gas phase of inorganic elements during wood combustion(Ⅰ):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quantification methods[J].Energy and Fuels,2006,20(3):964-978.
[17]Zheng Huaibing,Peng Xujian,Zhang Minxia.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containing gases release during com-bustion of main arbor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of China[J].Procedia Engineering,2013(52):645-651.
[18]Zeng Taofang.The ratio CO/CO 2 of oxidation on a burn-ing carbon surface[J].Combustion and Flame,1996,107(3):197-210.
[19]張衡中.碳酸鹽分解溫度的變化規律[J].有色金屬,1994,46(3):58-60.
[20]劉光啟,馬連湘,項曙光.化學化工物性數據手冊[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3.
[21]劉兆平.堿性物質對生物質混煤燃燒及污染物排放特性影響規律研究[D].山東:山東大學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2009.
[22]聶 虎,于春江,韋 威,等.生物質燃燒硫遷徙規律試驗[J].太陽能學報,2011,32(11):1671-1676.
[23]Knudsen J N,Jensen P A,Dam-Johansen K.Trans-formation and release to the gas phase of Cl,K,and S during combustion of annual biomass[J].Energy & Fu-els,2004,18(5):1385-1399. |
